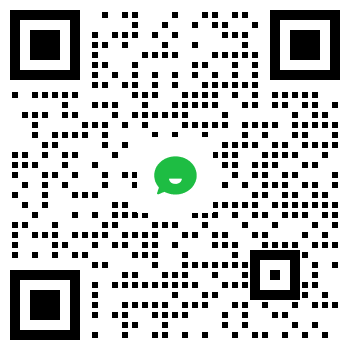来源:绿研所
日韩跨境碳出口计划引争议,CCS 技术面临多方质疑

日本和韩国正在酝酿一项引人注目的气候行动计划:将日本和韩国捕集二氧化碳出口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,并注入地下深处封存。
这意味着东亚的碳排放或将跨越重洋,在东南亚地下“安家”。
这一设想听起来新颖,但也引发了令人好奇和争议:日本、韩国为何打算碳运出去?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什么愿意接纳这些?
有哪些力量在推动跨境碳出口,有哪些人在担忧?关键的技术瓶颈和现实质疑有哪些?
更进一步,碳捕集与封存(CCS)究竟是低碳转型的有用工具,还是让化石能源续命的权宜计画之?
01 日本、韩国为何将碳“出口”?
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主要经济体,均已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中和目标。但在能源结构尚没有根本转型的情况下,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,确保能源供应和工业发展,成为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。

为此,政府层面将碳捕集与封存(CCS)技术视为关键路径之一,特别是在短时期难以完全脱碳的产业中发挥“兜底作用”。日本明确指出,CCS是实现净零目标“驾驶员”的工具,尤其在电力、工业等高排放部门,是当前这一体系的“零碳驱动器”。与此同时围绕CCS的部署,日本已制定了国家级技术路线图:
到2030年,实现每年600万至1200万吨的CO2封存能力;
到2050年,将CCS的年度封存能力提升至1.2亿至2.4亿吨,相当于其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0%–20%。
韩国也将CCS纳入其“国家战略低碳技术组合”,用于应对发电、钢铁、水泥等难以实现的电气化产业排放。由于韩国国内供给长期封存的地质空间有限,近年来积极推进与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的边境CCS合作,欲通过海外封存来弥补本国资源短板。
事实上,日本与韩国均选择向海外“埋碳”,除了出于技术体系设计的需要,更直接的动因来自于两方面的限制:
地质条件有限:本土不具备进行大规模、长期安全封存的地质结构。
公众接受度低:在建设二氧化碳注入设施时经常遭遇社区反对,项目推进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。
相比之下,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与印尼,拥有广泛分布的枯竭油气田与深层盐水层,构成了天然的“地质碳储存库”。相关研究估计,该地区具备超过百亿吨级别的二氧化碳封存潜力,可满足日韩等国未来几十年的“碳存储需求”。

除了技术原因,经济因素也是日韩推进碳排放战略的考量。CCS本身就伴随着高昂的成本,从捕集、压缩、运输到投入,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投入。在推进CCS不仅技术挑战大、社会成本高,还存在项目落地周期长、投资回升率低等问题。因此,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区域协作,可以更广泛、高效地完成CCS工程目标。
以2023年日本政府支持的CCS行动为例,已经启动的9个项目中,有4个计划将捕集的二氧化碳出口至海外封存,包括马来西亚、叙利亚、甚至中东国家的近海油气储库。这一行动不仅推动日本CCS路线从国内转向其他外部区域合作,也说明“碳出口”政策已被正式纳入其国家气候体系政策。
这一决策重新塑造了CCS的地理格局,也进一步引发了围绕全球双边责任、公平性与气候正义的深层次讨论。
02 区域竞争:马来西亚与印尼的“碳存储”博弈
当前,东南亚接收国通过立法为CCS提供政策支撑。
2023年,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法规,允许CCS运营商将最多30%的本国地下封存容量用于封存境外来源,这意味着“区域碳封存中心”的角色竞争日渐激烈。
在此背景下,马来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提出了避免竞争升级的措施:谁能率先建立商业化CCS基础设施,谁就可能在未来碳捕存服务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。
更进一步,这些国家都尝试通过碳封存获得三重收益:
1、引入国际低碳资金,缓解财政压力;
2、带动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服务(工程、运输、监测);
3、提升其在区域气候合作中的话语权。
简言之,马来西亚等国家希望不单单是“为他人埋碳”,而是在打造未来可能成为新型主权收入的产业服务体系。这些国家看重的不仅是每吨碳封存的服务费,更是一个即将崛起的区域性、跨境性“碳储存经济体”。
民间批评 VS 政府支持?
继马来西亚之后,印尼将CCS视为国家能源转型的新增长点。印尼政府公开表示,希望“快速推动”本国CCS产业发展,并在官方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求会谈建设为“亚洲碳储存中心”。
目前,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已与韩国国家石油公司(KNOC)及多个跨国能源企业签署了协议,计划开发覆盖捕集、运输、注入全链的CCS项目。
同样,对印尼而言,这不仅是一条路径,更是一条战略性产业投资——可吸引国外技术、资金流入,发展本土封存、运输、检测、监控等服务体系,培育“碳储服务业”的新活动。
跨国联盟:亚洲版“碳物流合作网”正在形成
这一跨境碳转移链条,是由政府、国家石油公司、跨国能源联盟和政策智库构成的“碳合作联盟”共同推进的。
其中,日本和韩国政府居于核心地位。日本经济产业省牵头推动的“亚洲零排放共同体”,目标是建立一个区域内可合作的CCS平台,以帮助日本将未来至少10%的海外存在的碳排放封存。
东亚智库如东亚经济研究院(ERIA)积极牵线搭桥,与各国政府共同建立“亚洲CCUS网络”,推动标准协调、技术转移和重点项目落地。
跨国企业方面,日本JAPEX、美国埃克森美孚、韩国KNOC、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、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结盟,推动上百亿美元规模的跨国CCS投资计划,并称这些项目将“成为实现亚洲净零排放的关键抓手”。
然而,正如许多国际环保组织所指出的——最支持CCS的,主要是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公司。目前全球大多数CCS都建在燃煤电厂、天然气田或炼化装置旁,从而延长化石项目消耗或提高油气采收率(EOR/EGR)。一些观察者初步解读为:化石行业在借CCS技术避免排放路径寻求“新合法性”。
2024年3月,马来西亚与日本的自然之友(地球之友)等非政府组织发布联合声明,直言不讳地称这种碳转移方式为“碳殖民主义”。自然之友马来西亚主席米娜克希·拉曼(Meenakshi Raman)表示:
“富国应承担造成气候破坏的责任。如今,日本等国家不仅不愿意这样做,还试图将二氧化碳排放本身转移给他国,将建立碳垃圾场。这不是合作,而是剥削。”
她同时指出,马来西亚政府本应将有限的地下封存资源优先用于国内工业,而不是“变相出租国土”来兜底他国碳债。
03 质疑与反驳:碳能埋,但正义与信仰埋不了
2024年9月,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一场气候抗议活动中,一位年轻抗议者高举标语,上面写着:“CCS,又是一个假解决方案吗?”这句话尖锐的质疑背后,最重要的是公众对跨境碳捕集与封存项目的深切不安。
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认为,所谓的“碳出口——封存合作”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,而是富国借助技术来利用祖先的化石燃料、转移责任的“绿色正义”。在他们眼中,这并不啻于新形式的“碳殖民主义”。

支持者说:双赢是现实,技术在进步
面对上述批评,支持CCS的政府和企业反复强调:这是一种“双赢”的现实策略,而不是责任外包。
一方面,日本、韩国等国家为支付捕集与封存费用,能加速实现本土承诺,减少碳排“硬脱钩”的经济震荡;
另一方面,印尼与马来西亚等“接碳国”获得可观的资金、技术输入与基础设施投资,有助于自身低碳产业发展;
同时,大多数跨境项目的创业风险和控制成本,实际上都由项目主导者承担。
正如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所表达的,这不是“代人买单”,而是“借力发展”。
然而,站在当地民众与基层社区的角度,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。
民间风险忧虑:谁来为地下负责?
尽管跨国CCS已形成真正的“资源互补”,但承受地下风险的是被封存地区的人民与生态系统。
环保组织警告:在缺乏信息公开、环境评估和公众参与的前提下,境外二氧化碳被永久注入地下,将可能带来长期不可逆的环境问题,例如:
地下CO₂泄漏;
地质结构稳定性受扰;
土壤和地下水污染;
渔业和农业生态影响等。
一些批评声音指出,CCS项目决策过度“上层推动”,而社区知情权与参与权严重缺位。多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(EIA)文件未公开征求意见,周边社区甚至不知道自己头顶将封存来自他国的“碳债”。
信息缺乏透明,公众无法参与,引发了对“气候正义”的担忧以及焦虑。
技术难题: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“成熟”
除了政治与责任问题,跨国CCS项目还面临大量现实与技术障碍。
首先,技术本身尚未成熟到可以大规模复制的阶段。尽管CCS早在上世纪末就被提出,但全球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大型CCS项目仍然寥寥无几。
一项2020年研究指出,全球超过80%的CCS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或中途夭折。 主要包括:
1、捕集效率偏低;
2、成本控制困难;
3、封存安全性难以长期保障。
特别是在边境封存的新情况下,经验更加有限。例如,日本将二氧化碳从本国运输至东南亚,需建造专用的液化二氧化碳运输船、冷藏舱、装卸码头等复杂设备设施。
目前,该行业仍处于示范验证阶段。2023年,日本建造的液化二氧化碳运输示范船“Excool”号在海上航行。该船全长72米,1450立方米的冷冻二氧化碳罐,用于验证海上运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(日本正计划通过海运将捕集的二氧化碳运输至马来西亚等地封)——但规模远不能满足商业化需求。
而运输过程中必须保持低温高压状态,这不仅消耗能巨大,还需要满足极高的安全标准。整个系统稍有泄漏或温控故障,都可能引发事故。
此外,大量研究指出,CCS本身就是“致命的吃电”。为了运行捕集装置,船只往往需要消耗多消耗20%~30%的化石燃料,导致“为了减少碳而排出更多碳”的尴尬局面。
这也是为何CCS被戏称为“电力系统的黑洞”。
其次是安全与监管问题。将数以百计的二氧化碳压到地下,需要确保这些气体能够永久留存数百年甚至上千年,不泄漏。
封存的长期稳定性存在不确定性:如果将来发生泄露,不只是前功尽弃,还可能对周边生态和居民造成潜在的破坏。谁来对这些封存库长期安全负责,同样悬而未决的问题——是由排放国、日本承担,还是接受国、马来西亚 印尼政府?
04 “转型工具”与“延命借口”之争
关于CCS,争议的核心在于它究竟是一种“必要过渡”,还是“变相续命”?当前争议颇多~
支持者观点:
对于钢铁、水泥、化工等难减排行业,CCS是唯一成熟可行的深度脱碳路径;
国际能源署(IEA)等机构也在全球净零路线图中保留一定比例的CCS,特别是BECCS和DAC等“负排放”手段;
在能源结构尚未完全转型的国家,CCS可为化石发电提供一个逐步退出的“缓冲期”。
反对者观点:
CCS至今仍未实现广泛商业化,成功率低,技术不确定性高;
它往往被化石能源企业当作延续自身商业模式的借口,而非真正的减排承诺;
巨额投入可能挤占本应投向太阳能、风能、储能等清洁能源系统的资源;
更重要的是,CCS无法解决化石燃料带来的生态破坏、大气污染、水资源浪费等系统性问题。
环保团体甚至将其称为“绿色伪装的挡箭牌”。他们指出,
“每投入1美元到CCS,都是对气候行动窗口期的浪费。”
05 最后的判断,仍留给时间与行动
从日本、韩国将碳排“出口”到马来西亚、印尼的计划来看,CCS已不仅是一项工程技术,而是一场跨国博弈:涉及气候责任、发展权、公平性、地缘关系乃至生态主权。
这些跨境项目,可能在未来构建起区域性合作减排的新样板;也可能因为风险、成本、社会反弹而沦为气候治理的又一个失败试验。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:
碳可以埋,但责任不能藏。技术可以试,但正义不能妥协。
CCS可以存在于温室气体解决方案工具箱中,但不应成为掩盖气候不公的遮羞布。
真正值得投入的,不是把碳挖个洞埋掉,而是从源头上让它少产生。
特别声明:本网站转载的所有内容,均已署名来源与作者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若有侵权,请联系我们删除。凡来源注明低碳网的内容为低碳网原创,转载需注明来源。
-
1
-
2
-
3
-
4
-
5
-
6
-
7
-
8
-
9